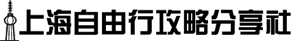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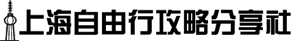
一分真,九分假
有点长,别当真
上海花园不在上海,而是西南小城里的一个老小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城开始修建第一批商品房,上海花园便是第一批之中的一处。在当时,能在这里面买上一套房的,都是条件十分优越的家庭,虽然直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了高楼林立的小城中一座被人遗忘的旧事。
我第一次来到上海花园,是来参加英语补习班的。
听邻居的阿姨说,有位姓冯的英语老师在这里开了一家补习班,教得特好。时值我小学四年级,妈妈觉得是时候给我打下英语基础,便找到了这里。
补习班在上海花园3栋一楼,是由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改的,一个房间一个教室,客厅用来停学生们的自行车,饭厅是唯一一间大教室,而厨房改成了一间只够容纳两人的办公室。
补习班是由冯老师和他的老婆一手办起来的,他的老婆的我们叫MISS黄,是一个皮肤很白的很温柔的女人,戴着小小的金丝框眼镜,说话的时候总是微笑着,几乎从不对学生发脾气。
上海花园里栽满了一种树,树干往上长,枝条往下垂。我刚去的时候,这树还没我高,等到我高中毕业,它们已成长地蔚然深秀。
那时候我们补英语课,是一三五学校放学后去上课,六点到八点,然后周日早晨再上两小时。刚去的时候年纪又小,还有几分羞涩和拘谨。不过一个月之后,我已经成为了补习班的一大“毒瘤”。
小胖子和小板凳
当时来补习英语的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学很久,一学期或是半学期之后便不再来了,很多是因为上课时间太过密集,家长或者学生觉得小学没必要抓得这么紧,很累。
于我而言,冯老师那儿从来就不是一个无聊、累、无趣的地方。
班上有个小胖子,男孩儿,长得特别嫩,从小学开始就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长得人畜无害的样子。
我叫他小陈。
小陈很小器。
大概每个阶段都有个和我八字不合的男生被上帝派来针对我,小陈就是补习班的第一个。我们俩不能相安无事地说上两句话,一般第二句开始就动手,第三句的时候已经互相拿起了手边的小板凳开始互砸。
小陈家里不是本地人,说话有一点点重庆口音,他总是用着我听不顺耳的声音说:“你就是瓜娃子,天天只晓得打别个,除了歪你还会啥子?”
现在想来他说的也不无道理,甚至颇为精准。可那个时候的我,自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你都这样说我了,我不动手收拾收拾你一下岂不是有悖你对我的评论?
还没上课,我将教室的门关上,把小陈推到墙角就开始揍。他也不甘示弱,一边冲我拳脚相加一边破口大骂,像只嘴臭还被扼住喉咙的肥蚂蚱。
有人打小报告,冯老师气势汹汹地从办公室冲过来,一脚踹开了教室门,怒目圆睁。
“shut up!”冯老师跟拎小鸡一样一手一个,把我俩给拎到了办公室。
MISS黄此刻正在办公室里备课,满脸慈爱地看着满脸衰相的我俩说:“你们又打架啦?哎呀Debby你是女孩子,要注意一点啦。”
我说:“是他先骂我的!”
“她先打我的!”
“你不骂我我会打你吗?”
“那还不是你讨骂!”
“Shut up!What are you guys doing?”冯老师肥肥的脸由红转紫,被气得眼珠都快蹦出来了,我俩终于住嘴了。
冯老师让小陈先回教室,把我单独留了下来。
我坐在狭小办公室的小凳子上,接受无视我的酷刑。
冯老师和MISS黄继续备课,我坐在一旁不知道该干什么,偷偷摸摸地烦了一下桌上的教材,被冯老师一个眼神杀射过来,秒怂。
“Debby你要是再在教室里这么闹,下课后多留三十分钟。”冯老师知道搬家长出来是没用的,他也一向推崇学生的自我发展,所以一般都会和我们本人解决问题。
我当时在补习班里,是记单词和背课文最准最快的一个。往往我十分钟记完所有单词,就开始前后左右地骚扰其他同学和我聊天,听写完成后我全对回家,留下被我祸害的同学们罚抄单词。
在我的补习生涯里,有这样一个印象深刻的画面。
我所在的班并不是一直都冯老师授课,有些学期是年轻的实习老师,有些学期是MISS
黄,有些学期是冯老师。
那位年轻的实习老师叫Lynn,是个个子小小的姑娘,长了一张娃娃脸,脾气特别好。
Lynn很宠我,她知道我背单词快,还会找别人说话,每次也只是走过来轻声细语地说:“Debby你背好了就背背明天的,别打扰别人啊。”
“毒瘤”如我又怎么会轻易听话,于是我往往应承下来,10秒后又开始发病。
冯老师有时候没课,有时候在给我们隔壁高年级班上课,但只要我们班开始背单词了,他就会默默溜达到我们教室门口,阴沉着脸盯着我,以免我妨碍其他人。
很多次我找后坐同学聊天,我的头顶缓缓出现一片阴影,然后一只宽厚有力的手“啪”一声拍上我的头顶,接着就是冯老师熟悉的嗓音。
“张xx,我叫你别影响别人你听不懂吗?”冯老师特别生气的时候就会直接用四川话叫我的大名,一般这种情况下我都会真怂,急忙坐端正接受一阵眼神批评。
每每这个时候,安静的教室里都会响起一个带有口音的嘲笑声,正是小陈发出来的。
现在的我已经忘了,是从哪一天开始,小陈突然就不再来补习班了。冯老师说他转学了,我听学校里他的同学说,好像是搬家了。
从那时开始,我再也没有见过小陈。
我们没有手机,没有互换电话号码,甚至我连他的真名都不记得,当了两年补习班的互怼同学后,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
哦,除了墙上刻下的互相骂的一连串脏话。
“你们就是笨蛋兄弟啊”
升上中学以后,我们补课的时候集中到了周末和寒暑假。
中学开始,补习班的人越来越多,却基本没有我认识的了。
广大第一次来班上的时候,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内容十分饱和,就和他本人的额头一样。
他来得有些迟,坐在了第一排。
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身后跟着另一个人,和昂首挺胸满脸膨胀的广大相比,他从善如流地走进教室,很低调地坐在了广大旁边。
那时是冬天,每个人都穿着深颜色的厚棉衣,教室泡在暖气里,所有人都目光呆滞昏昏欲睡。
除了L。
广大是继小陈之后,补习班里我的第二个死对头。
之前和小陈只是在地上打,我和广大是站在桌子上打,跳着打,坐着打,上课打,下课打。鉴于我俩战斗力实在惊人,冯老师勒令我俩不准坐在一起。
从此,教室这头一个我,教室那头一个广大,两足鼎立的局势就此形成。
Lynn给广大取了一个很能衬托他气质的英文名字,Dan。L和广大一起来的,Lynn也顺便给他取了一个广大的情侣名。
“要不,你叫Ben吧?”Lynn满脸期待地看着L,L很害羞,本来在暖气房子里浮现出的高原红颜色更深了一层,他没有在意班上其他同学的嗤笑声,很用力地点了点头。
因为这名字,我笑了他俩好多年。
广大说:“我蛋我怎么了我?你一个呆逼比我好哪儿去?”
然后就是又一场席卷整个上海花园的战役。
然后就是L跑出来站在我俩中间,满脸无奈地劝架。
那时广大很喜欢听一个讲鬼故事的电台节目,叫做“张震讲故事”,他总会在手机上下载几集带来补习班,没事儿的时候听。
彼时我和广大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打友”的状态,每天依旧为了小事闹矛盾,同时也是同流合污的好战友。
为了实时“监控”两大“毒瘤”的动态,冯老师下达了另一个指令:Debby和Dan上课只能坐前两排。
上有政策,下面也没带怕的,因为Lynn脾气好到我俩根本不怕她。
到了夏天,补习班的空调总是开着,暑假的时候我最期待的事就是跑去补习班吹空调,有时带上几本漫画书,有时跑去办公室和老师聊天,因此补习班成了我的小基地,每次去都跟回家一样熟悉。
补习班是在一楼,本就一直被树荫罩着,空调一开久了,便有些过于凉了。
背单词的十几分钟里,教室是最安静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ABC”的默念声。
广大偷偷摸出手机,贼眉鼠眼简直是他本人,冲我猥琐地一点头,打开了“张震讲故事”。
恐怖片万年不变的旋律从桌子下传来,先传遍了整间教室,最后才传进了Lynn的耳朵。
Lynn走到我俩旁边,我憋着笑别过脸。广大满脸无辜地指着我,Lynn把教材卷成筒,轻轻在我头顶砸了一下:“Debby,你怎么这么调皮!”
用书打头一定是上海花园的祖传手法。
Dan笑得更加猥琐了,我眼疾手快地从他抽屉里把手机掏出来,扔到桌面上,张震悠悠忽忽的声音更加清晰,Lynn实在受不了,没收了他的手机。
那之后,我们又用了30秒密谋了一场“骚扰电话”,具体步骤如下。
先借到Lynn的手机,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全部删除。上课后,轮流给Lynn打电话。
她接了几次都没人应,开始怀疑起这个号码,越看越熟悉。傻白甜小老师福至心灵,伸手到我面前:“Debby,手机拿出来吧,又是这些小把戏。”
我眼看逃不了上交手机的命运,于是从善如流地把前后左右几位同学的手机全部揽过来快速交到Lynn手上。面对我的背叛同学们欲哭无泪,Lynn却被这个无赖行为逗笑了,一边收拾手机一边说:“你们这些小朋友,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笨蛋兄弟要来上海花园上课的话,必须得坐公交车,走去公交站台的路线和我回家顺路,于是每次放学我们都一起走。
路上会经过一条商业街,那时小城里的商铺促销都很野蛮,几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站在店门口,冲来往的路人不停招手叫卖,若是身姿再妖娆点,表情再挑逗点,环境再魅惑点,。
一次补课,刚好赶上了某个节日,各个店家使出了看家本领搞促销,都拿出了恨不得把收银台都卖了的气势,连背着书包的我们几个都不放过。
“小兄弟,来看看,这里打五折了!”一家女装店的店员硬是拉着广大推销,我们其他人绕过他,满脸嘲讽地把他往店里推。
广大硬是把书包带从店员手里给扯了出来,这才逃过了一劫。他匆匆追上我们,大手一挥就想打我的头,可他的脚下传来一声微弱的“叽”。
旁边正欲上前揽客的店员指着广大脚下的东西尖叫了一声:“耗子!他踩着耗子了!”
说时迟那时快,还不等广大看清楚他前脚踩的到底是不是耗子,我后脚就给它补了一脚。
嗯....软软的,有点溜....
那一瞬间,我分明感受到了身上所有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跳得比袋鼠还快,根本没勇气回头看一眼那只被我们踩了两脚的耗子后事如何。
我这辈子,最怕的东西就三样,耗子,蛇,和鬼。
那之后,我们对那条街有了阴影,耐不住回家必须从那儿过,从此以后都跟过雷区一样,一脚一个脚印地趟过去。
初中三年,我们就在无数个昏昏欲睡的下午,拿着中性笔在墙上写满了对方的坏话。
“这么巧,不如交换个名字”
在一起度过了几年的补习班时光后,我和广大还有L,来到了同一所高中,很巧,还是同一个班。
彼时我被班主任任命为第一任班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全班同学的座位誊抄一份姓名表。
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记住L的真名叫什么。
因为有一个男生的名字太像女生了。
我和L之间不像和广大,我们之间的所有有限的交流都是因为广大,所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我和L是从没有说过话的。
我的座位在最外面的一列,L的座位在最里面一列。第一节课的课间,他从教室另一边跑过来找我,说要借我的姓名表抄一份。
说句实话,这是我记忆中他真正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已经记不太清那时的L长什么样子了,即使我想尽量还原,也没有照片或者影像供我参考,这是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
要说唯一还记得的,大概是他绕到我的桌子旁,很有礼貌,很客气,并且在下一个课间就急匆匆地把姓名表归还给了我。
座位每周往左移一次,第二周,原本坐在教室两边的我和L,成了“同桌”。
一个班只有三十几个人,一人一桌,我和L中间隔着狭窄的过道。具体有多狭窄,若是中间站个人的话,就会挤得慌。
高中时的L好像和我之前在补习班认识的不是同一个人似的,我发现他并不是少言寡语的人。
L长得很有优势,很浓的眉毛,眼睛很黑,有段时期脸上还有几点雀斑,鼻子高挺,皮肤很白,笑起来的时候傻气又温暖。
所以有很多女生喜欢他。
L成绩不错,但不是特别聪明那种,他的聪明都用在了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之中。
那年春天,我们的教室还在一楼。
学校周边的野猫总有几只偷偷溜进来,从食堂里顺走一点吃食。春天,一个万物繁殖的季节。
L和我又到了坐在教室两头的日子。
他的座位在窗边,典型的男主角座位。
窗外的野猫开始叫春,彼时在上晚自习,全班没有一个人说话。L从昏昏欲睡中突然惊醒,抬起脑袋像个四处探头的土拨鼠,然后一窜就趴在了窗口,学着窗外的猫叫和它聊起天来。
班主任悄悄从后门进了教室,他是个待学生十分友善的英语。
班主任踱步到L身后,沉默地注视着还在和猫咪聊天的L。
全班同学抱着看热闹的心情,十分默契地沉默着憋笑。
“L,你遇见你兄弟了?聊得这么亲热?”班主任拍了拍他的肩,满脸的不可思议:“和只猫你都能聊,可以啊。”
L脸顿时就红了,黑黑的眼睛有些躲闪,不好意思地笑着,然后默默坐回了位置。
L是个很喜欢恶作剧的大男生,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做过小男生。
他会把结痂的旧皮撕下来扔我桌上,实在是非常无聊。更无聊的是,他还会把擦完鼻涕的卫生纸混在干净的纸里递给我。
我曾一度怀疑,这个L是不是被什么妖魔鬼怪上了身,前后差别也太大了点。
“你永远都是风雨小蝴蝶”
高中的周末我们会照常去上海花园补课,因为现在大家不仅是补习班同学,也是高中同学了,冯老师管起来就更不好管了。
补习班的学生越来越多,冯老师又在上海花园里租了一套房子,高年级的教室就全部搬过去了。
上了高中之后,冯老师很少叫我们的英文名,因此“笨蛋”“呆逼”这些名头,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记忆。
我有一个发小,女孩子,矮矮胖胖的,长得有些像朴信惠,性格特别傻白甜,很多时候叽叽喳喳又好动,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梦,那我们就暂时叫她小蝴蝶吧。
小蝴蝶高中没和我们一个班,后来才转到我们班的,不过补习班里是和我们一起的。
L的很多初中同学都在我们学校里,基本每个班都有他熟人,他也经常去别班串班。而且他尤其爱多管闲事。
记得高一的某天,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到我们班玩儿,结果玩着玩着就和我们班的一个高个子男生打了起来。L当时正好在教室后,拿着扫帚簸箕在扫地,眼看着就打了起来,他扫帚都来不及放下,就冲上去劝架了。
一阵混乱之后,小蝴蝶也跑到我们班上看热闹,兴奋地拉着我说:“L好有趣啊,我好像喜欢L。”
小蝴蝶喜欢某个人的话,全世界都知道。
很快,L也知道了这件事。
我们学校隔三差五就要举办一些演讲比赛,话剧比赛什么的,校长说要让学生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可苦了不敢抗命却还要赶教学进度的任课老师们。
托校长的福,我们很多个晚自习都可以悠哉地坐在礼堂里唠嗑看节目。
演讲比赛那天,我将自己写了两天的稿子最终拿给班主任修改,然后紧张地坐在礼堂第一排候场。
文科班有个男生转过来,找我借稿子给他看看,说是想了解一下大家都写的是哪些方面。我没有多想就递给了他。
他若有所思地看完了我的稿子,然后默默递给我,一句话也没有再说过。
除了他给老师申请早点上台演讲,说是不想耽误晚自习。于是老师把他排在了我前面。
他开口第一句,便给了我一个猝不及防的下马威。
我整个稿子的开头和他的一模一样,我们都引用了同一个人说的同一段话,一字不差。
十几岁的我没有强大的知识储备与经验,临场时更是被打击得不知所措,在有限的几分钟内,我做了一次争分夺秒的冒险。
我硬生生将点明整篇演唱主旨的段落删除,重写拟写了几十字潦草的开头,然后将全稿顺序重新排列,硬是给变了一个主旨内容。我不确定自己的临场是否足够优秀,能讲清楚我的想法吗?能顺利传达吗?能被认可吗?
我就在这样纠结的胡思乱想中结束了这纠结的几分钟。
小蝴蝶坐在第二排,也替我紧张着。
比赛结束后,肩上的重量一下卸了下来,我接过小蝴蝶递来的水,瘫坐在了位置上。
她欲言又止地盯着我看,凭我对她多年的了解,她动动脚趾我都知道是要放屁还是吃饭。
我转头看着她说:“你要说什么吗?”
她点了点头,有些惆怅:“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她握紧了手里喝了一半的塑料瓶:“L不喜欢我。”
“......哦。”
“他好像喜欢你。”
“唔......不会的。”
小蝴蝶的这份喜欢,持续了很多年。她本就是个咋呼小女孩样,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定只是暂时的喜欢吧,一定不是真的吧,都是可以用来开玩笑的吧。
实际上每份喜欢都不能用来开玩笑,她只是用玩笑来做盾,你刺向她,还是会疼的。
小蝴蝶和广大这两家冤家仇人,比起我和广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今时今日一谈起广大,小蝴蝶对他的评价还是那两个字:“傻逼。”
广大其实对小蝴蝶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很爱逗她,一逗就会接招。男孩子下手也不知道轻重,毕竟不是每个女孩都像我一样皮糙肉厚,总是逗得小蝴蝶真生气了还不收手,从此结下梁子冤家路窄。
上大学之后一次过年,广大回来了,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他问我和小蝴蝶:“我想追个学妹,你们给我想想办法呗。”
小蝴蝶玩着手机头也没抬:“别追了,你这样儿的还是算了吧。”
广大又好气又好笑,这么多年也算是摸着点小蝴蝶的脾气了,可怜巴巴地转头问我:“我什么时候又惹到她了?”
“你的存在本身对她来说就是烦恼。”
小蝴蝶笑了,广大叹了口气,郁闷地埋头继续吃饭。
我也忘了具体是哪一年,小蝴蝶突然对我说:“我不喜欢L了。”
她以往也这样说过很多次,我没当回事儿,敷衍地应了一声。她见我态度冷漠,着急地抓着我说:“我真的不喜欢了。”
后来我大概明白,对她来说,喜欢上L本就是个突发事件,没想到却发展成了长线暗恋,为他纠结了多少年,又成长了多少,到最后,通通换成了一份带着酸涩的讨厌。
现在的她也经常对我说:“我现在真的讨厌他,你看他对谁都那样,有没有心啊。”
小蝴蝶还是爱嘟嘴,却不爱和我见面了。
“唔...可能还是留下了点什么”
高中毕业的时候同学聚会,L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参加,我没说话。
他在喧闹中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我感觉,整个高中是不是都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啊?”
整个三年,是不是真的没给我留下什么东西啊?
我参加了很多比赛和活动,做了许多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事。和班上的活宝同学打了架,初中部的小胖子一直到我毕业都还记得我的名字,寝室我们从三楼一直搬到了一楼,我还记得上铺的同学总是把水果刀和没洗过的袜子放床头,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我头上。半夜躲在厕所里玩三国杀,玩到凌晨2点,还被对面楼的男生发现了。
高中留给了很多回忆,却没有给我留下一个人。
高三后段时间,我和L基本没了任何交流,连最简单的打招呼都没有。这中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只是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小插曲而已,我们故事的主线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若是我的朋友同学看了我以上几段话,大概又会觉得我冷血又绝情了。
但一个人的心和感情是有限的,我就是要将那些事遗忘,因为我明白了我的最初和最终是什么。
而关于那些“插曲”,我现在没有心情再写出来。
这几天和高中同学聊了聊,我发现我的确是在选择性地遗忘一些东西,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很多事我都已经记不清了,只有几个模糊的印象。
至于我和L是怎么疏远起来的,我更是连个印象都没有了。
从高中到今天,七年的时间里,我心里只有一个结始终解不了。
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见,见的都是物是人非。
冯老师回了加拿大,补习班也关了,上海花园门口被喷上刺眼的“拆除”字样。
L比起以前更加敞亮,已经是飞行员的他,依旧很瘦。小蝴蝶独自一人去了上海,广大在北京,不久后要到德国去了。而小陈,早已没有了音讯。
我待在这里一直发呆,有些事,还是留下了。
上海花园栽满的树叫做垂榆。
我想起了七年前他第一次找我借姓名表。
“你写的都是谁的故事啊?”L好像这样问过我。
我永远不会告诉你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