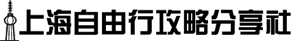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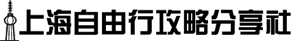
我家在一个老街区上。我爸我妈年轻气盛的时候很能干,算得上白手起家。他们那时候和我现在一样,为了一个人可以不顾一切,他们的结合是两家都不愿意承认的。对于外婆家来讲,我爸没有什么牛逼的文凭,不配他们的书香世家;对于祖母家来讲,我妈娇生惯养,不同他们偏爱的好生养之流。往往能讲的故事都不会有顺利的经过,往往能讲的爱情故事都源于老一辈的固执。总之他们没有得到老一辈一丝一毫的祝福和援助,一切从零开始。
经济的跨越最直接表现在住房上,我出生后那十年搬了三次家,一路搬到这里——当时又大又新的单元房。所谓饱暖思淫欲,后来家里纷争种种就不提了。总之自打我记事起,我就住在这里,看着这楼一天一天变老,看着周围一天一天升高。
老街区肯定有老街区的样子,就像北京的四合院有瓦有树有门洞。邯郸老街区的特色就是连成线组成片的按摩房理发廊。
在一个冷落的街口等红灯,我趴在车把上抬头看,前面就是老街区了,一眼望去依然没有灯,但并不是一昧的黑暗。路边的发廊爆发出绒毛粉和青空蓝的光,莹莹地照着风尘仆仆的大路,像是圣诞节的深夜,客厅灭了灯,圣诞树上披挂着的小彩球莹莹地发着亮。又像冬夜大雪里的一中食堂,巨大的红色滚动广告牌把整栋楼包裹起来,在周围肃静漆黑的雪地上明珠一般闪着耀眼的光。
虽然才十八,凭着目睹这些发廊的成长变迁,我可以说是一个老邯郸了。最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学生,从没有注意过街边这些奇奇怪怪的店,她们在我眼里只是为了让我眼熟“按摩、理发”等汉字用的。后来有一天一个混混同学很牛逼地告诉我,他看见教我们写字课的老师进了一家发廊。一瞬间,我醍醐灌顶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混混同学那双真诚的渴望传播真相的眼睛和夸张的嚼了屎一样扭曲的表情严重刺激了我腺垂体和肾上腺激素的分泌,让我对这些小店有了初步认识。那个混混是我们班发育较好的一个,我还和一群女生玩抓奶龙爪手和猴子偷桃的时候,他就在多媒体上的投影上表演食指插拳头了。据说他也住在那个街区,而且楼下就是发廊,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女人们的叫声;也有人说他姐姐就是只鸡,我倒是见过他姐姐,家长会上浓妆艳抹,穿着当时最流行的牛仔布短袖和黑色皮面短裙。当时幼小无知的我看了她一眼,仿佛看见一团白白的肉,吓得赶紧调头走了。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留意这些店。一开始都是挂着牌子的,什么什么发廊,什么什么按摩,一条街上牌子相连成趣,一片欣欣向荣。其中最有文化的一个叫“老地方”,大概取老地方见之意。过了几年市里严查,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警车嗡嗡地叫唤,一阵子后,所有牌子都没了,但门照开。只是街上光秃秃的,只有零零星星的复印店桶装水店挂着牌子。我想没了牌子后那些男人再也没法说今晚去什么什么发廊什么什么按摩了,只有“老地方”是有远见的,不管没有没牌子,她永远都是男人口中的老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出去玩,突然看到一群男人从面包车上下来,手里拎着棍子管刺。他们踹开一家发廊们就开始砸,里面的连拦都不敢,净从后门跑了,留下一个空店给他们砸。街对岸站着成排的围观群众。我离得比较远,又走了两步看到前面已经是一片狼藉,碎玻璃和红粉的衣裤扔在街边,几辆面包车也停在街边,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之后的几天老街格外黑暗,因为晚上再没有哪家店的门是开着的,灯从推拉门里透出来洒到街上。过了一段时间,零星的店开门营业了,晚上又有了亮光,但是和以前比暗淡多了。
那一年,有的店重新营业后,开始用粉红的布帘装饰,光打在巨大的帷幕上反映出可人的色彩,仿佛靡靡之音。直到现在,晚上,还在营业的店照得街上红红绿绿,光是通过布帘反射来的,肥而不腻。
留下来的店都该叫老字号吧。我想,不知道店留了十年,人是不是还是那帮人。可能曾经最低级的站街现在成了妈妈,曾姐的现在已经夹着腿睡在别人的床上,曾经的老鸨都回了乡下老家给儿媳妇带孩子。那些男人们呢,估计都成了不折不扣的老男人。我这么想想,还有些许惆怅。
车子蹭着边慢慢悠悠骑过去,每到一家店门口三四个就往路边靠,我骑得很慢,她们靠近得也很犹豫,像扭扭捏捏的大姑娘要出来见人,仿佛等着我主动开口。直到我要骑过去才有一个或者两个急迫地“欸”一声,拖得长长的,偶尔会吹个溜痞的口哨。
“帅哥,帅哥!”声音的来源被我慢慢超过,甩到后面。我冲她们笑着摇摇头,其实每次从这里都冲她们笑着摇摇头。我不认识她们,我也不,我和她们唯一的接触就是“小帅哥玩玩啊?”“没钱。”
我写过一篇自以为是的文章,说这些女人很无助,很渴望炽热的爱情。然而此时此刻,我骑着车子从她们面前经过,眼角的余光看到她们游荡,她们坐着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我想她们应该不渴望爱情,生活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的认知里还有没有年华这个词?我不敢说。
老马识途,前面是街上最头的一家按摩店,就是原来的“老地方”。夜很黑,但是“老地方”在光亮里,像是在舞台上。我抬头看的真切,一个穿着黑色吊带裙的女人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翘着腿,一只手夹在两条腿中间,一只手摇着米黄色的蒲扇。她面朝我要去的地方,蒲扇要慢慢地摇才有风。我骑到离她最近的地方,看到她穿着长筒的高跟鞋。她要是站起来,一定很高,一定有万种风情。但她就是那样蜷缩着,也不看我一眼。然后我就骑过去了。
我见过世俗人家的少女,腿长,穿着类似旗袍的直筒裙子,露出一道细白滑嫩的腿。站在街边平房的商店屋檐下,那街上热热闹闹,各种正当的店铺洋溢着黄色的温暖的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各个店门口摆上桌子打着扑克下着棋。少女手捏一把圆形小布扇,尖尖的脸尖尖的眼,一眼从过往的人群中盯住了我,我正骑着车子心中一惊,尴尬地一笑,她却不觉尴尬,莞尔一笑,两叶眉似细瘦的柳,新生的月,清雅而明亮。
相比之下,少女比她敬业多了。天太热,俗世的女人卖够了,不想卖了,就卷缩在小板凳上,夹着自己的。世俗的少女卖弄风姿,她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带着傲娇,但是天下的男人没几个是东西,过几天不仅白白给人上了,指不定最后还要哭着求着让人上,似乎不做,爱就没了。
“你这赔钱东西!”如果我是他爹我一定这么骂道。
*作者:翟羿鹤,心林细语原创专栏作者。
版权声明:【本文由「心林细语」原创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匿名转载,否则视作侵权。】合作联系QQ:2483843068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