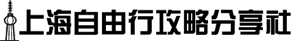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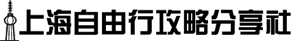
见习记者陈美玲 实习记者顾佳妮 丨文并图
穿行在七宝老街,商铺林立,熙熙攘攘,人潮涌动。这里,有的人来了,但很快又走了;有的人虽然留下了,却也熬不过岁月的变迁。但有的人,来到了这里,就不再离开。
沈渭滨就是其中一个。他从北大街到沟水弄,再到浴堂街李家房子,最后落脚于宝隆新村,转来转去,未曾出过老街范围。他已习惯于老街的味道,甚至与老街融为一体。艾青在诗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于沈渭滨,他始终守着老街,何尝不是一片痴心?
4月18日,《沈渭滨先生纪念文集》首发式在七宝举行。时值沈渭滨逝世一周年之际,七宝镇政府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了这次活动,纪念他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出的贡献,也传达了社会各界特别是七宝人民对他的缅怀之情。
1937年,沈渭滨像平常人家的子女一样,出生于七宝北大街22号。从小,他就穿梭在老街的大街小巷,对老街的一砖一瓦,对老街的左邻右舍,都是烂在心里般的熟悉。在七宝明强国民学校读小学的时候,他的书法、绘画尤为突出,极受语文老师喜爱。
初中毕业后,他决定潜心于绘画,报考了行知艺术师范学校美术专业,可惜未录取。而后,他苦于无学可上,经介绍,前往福建军区干部文化学校文教队当学员。1957年,,但仍不忘绘画理想。于是,他先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只是造化弄人,体检结果显示“色弱”,画家理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地破灭了。
但执著的他哪能说放弃就放弃?不能画画,退而求其次研究美术史也算一种满足。之后,他以调干生名义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万万没想到,该校历史系没有美术史专业。在转系、转学均无果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既来之则安之,并为此孜孜不倦,最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求学多次辗转,但沈渭滨的心一直留在七宝。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七宝中学工作,。繁重的教学之余,他又锁定了学术研究。每天学生熄灯后,他总要再看三个小时的专业书,几乎没有一天在11点前睡觉。后来,在报考著名史学家陈旭麓研究生落榜后,他将陈旭麓作为终身追慕的导师,不断向其请教学习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
1971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抗议无效后,他被关在了用木板隔成的两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隔离期间的他,尽管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思想仍纵横古今。
他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写道:“隔离之初,我怒不可遏。踢墙捶门,抗议不断。二三天后自知无用,稍稍安静。……我想虽然无书可读,但可以将平日读过的史籍默写梳理,凭记忆写点心得,也算不枉这类似牢狱的日子,给自己也给后人留点东西。”
因着这单纯的想法,他在长9.3cm、宽6.3cm的草纸上,写就了5万余字的《七宝沧桑》两卷和10万余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章。其中,《七宝沧桑》两卷被誉为1949年后七宝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七宝镇志。及至《七宝镇志》编纂的时候,他虽然不直接参与,但凡纲目制订、评稿、审稿,都参与其中,使得镇志的编写具有了较高的水准。
1975年,沈渭滨由于陈旭麓编写《中国近代史》人手不够,被借调到复旦大学。之后,他正式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远在杨浦,他仍然住在七宝,每次来回,要换乘三趟公交车,用时2个多小时。但他的家并未因此搬离,终其一生。
生于斯,长于斯,老街滋养了沈渭滨,沈渭滨也默默地守护着老街。
上世纪90年代,七宝古镇出现了拆除与保留之争。当听到拆除的说法,沈渭滨坐不住了,义正言辞地斥之为“岂有此理”。作为历史学者也好,作为老街的子女也罢,他无论如何都不希望老街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取代。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古镇,拆了就没有了!”
2000年,古镇在大家的拥护下保留了下来,并进入修复改造阶段。七宝老街修复文化顾问小组由此成立,年过花甲的沈渭滨当仁不让地成为其中一员。他说,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学问,写了那么多历史著作,却不及做这个顾问来得兴奋。他还说,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故乡。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是他一生心之所向。
正因如此,他对老街的修复倾注了大量心血,每周一次的例会他必到。他赞赏老街的修复思路,但不满标志性古建筑塘桥的修复,认为是亵渎文物,破坏明代桥梁的结构,还一直追问换下来的旧桥石去了哪里。对于设立张充仁纪念馆的建议,他拍手称好,还趁热打铁地给领导写报告。事后,他觉得此事“非常快慰”。
他对老街是认真的,认真到不愿意有一点点污秽沾染老街的边边角角。在老街修复过程中,有人掮着领导的牌头,以策划编辑老街旅游手册招摇撞骗。沈渭滨一眼识破,马上戳穿这个小把戏,如孩童般地感到“无比痛快”。
他对老街是负责的。在修复过程中,他情真意切地撰写了两块重要碑记——《修葺七宝老街碑记》和《蒲汇塘桥重修记》。到过老街的人们,或许没注意到,或许看到过,但无论如何,这两块碑记将永远立在那里,不仅记录老街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了沈渭滨与老街的不解情缘。
对于老街的评论,沈渭滨始终无法置身事外。有时,他在公开场合讲的话,甚至让领导有些尴尬,但尴尬之外,都是他对老街满满的爱。老街改造一新后,有专家批评老街是假古董,修旧不如旧,他马上站出来说,老街基本上是原来的格局。这种底气来自于他的一篇有关七宝格局的报告。
沈渭滨对老街常含着深情,所以他紧张老街的发展,关心老街的一桥一路。他说,人少的时候,他会饶有兴趣地上老街走走、看看,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亲近老街。或许,只有在老街,他才能听到故土最清晰的心跳。
在学界或在社会,沈渭滨有个雅称——“七宝沈渭滨”。据说,许多人为了探视他,或与他切磋学术,从全国各地或上海其他地区寻迹而来。七宝这个地名自然而然地就和他联系在一起,大家也称他“七宝名士”。
七宝镇党委书记马顺华在为《沈渭滨先生纪念文集》写序时,这样评价他:沈老师是继张充仁之后,又一个七宝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卓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就,是七宝文化的又一高峰。他续燃了七宝文化的香火,如果没有他,当代七宝文化将出现一个极大的空白。沈渭滨深爱着七宝,七宝人民也敬爱着他。七宝因传说的七件宝而得名,但在七宝,可能很多人未必能完全说得出哪七件宝,但对于第八宝,人们却非常熟悉,那就是沈渭滨,他们已经把他当作七宝的一张名片。
在那里,沈渭滨无人不识、无人不知。曾有传言:如果寄信给他,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上海七宝镇沈渭滨先生”,他就可以收到。因之,《文汇报》记者施圆宣还跟沈渭滨开了个玩笑,真真寄了一封略去小区门牌号的信。结果,他当然是收到了。
他的学生张国伟也说,以前,他们到七宝,随便路上找人问“沈渭滨家在哪里”,人家就会给你指路,你不知道他住在几楼几号都可以找到他。而去过他家的学生,都清楚地记得跑得飞快的92路,仿佛就是沈渭滨家的专线一样。学生们都觉得,沈渭滨是七宝名人,是古镇的第八宝。
沈渭滨在七宝中学任教多年,桃李芬芳。王孝俭是其中之一。读书的时候,他们亲切地称他为先生。在回忆老师时,王孝俭写道:“沈先生不同于一般学人,他对故里的爱和不满是交织在一起的,更多的是缱绻于自己的实际情感和生活习惯有所依恋的老街生活。”
每年的正月初五,是沈门弟子给老师拜年的日子。近三十年来,学生们风雨无阻地从四面八方、甚至从外地赶来给老师拜年,师生济济一堂,尽情畅谈,开怀大笑,情意浓浓。这也成为上海历史学界师生关系的一段佳话。
于是,微信兴起后,便有了“初五沈大大”的集结令。在七宝,人们习惯将祖父或尊者唤作“大大”,沈渭滨是七宝人,又是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和长者,所以大家尊他为“沈大大”,微信群因此得名。
:“在拜年相会时,老师一改在课堂上的严肃和正经,表现出和蔼、甚至带有童趣的另一面。谈起甲A、中超、意甲、英超时,沈老师会比划带球突破、起脚射门的场面,一板一眼的架势让人忍俊不禁;谈起新近上演的电影和电视剧,以及刚谢幕的央视春晚,评说明星大腕,圈点个中得失,沈老师近似专业导演的水准,让人钦佩不已;谈起学生各自的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他的叮咛嘱咐、语重心长更让人倍感亲切。”
不过,欢聚期间交流最多的还是有关历史的学问。沈渭滨会把出版的学术著作一一赠送给学生,并与学生交换研究心得,分享个中酸甜苦辣。
“初五沈大大”2014年创建后,入群人数越来越多,有沈渭滨在复旦大学带教的研究生,也有虽非复旦学子但其额外带教的私淑弟子,更多的则是就读复旦大学本科时听过他讲授“中国近代通史”等专业课程的学生。
谈起沈渭滨,学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老师上课极好,无论是上课的内容还是形式。学生张国伟回忆说:“听沈先生上课,就像听‘学术说书’,他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讲历史人物,讲得有声有色;讲历史细节,他讲得身临其境。比如讲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逼宫洪秀全:‘东王噶大功劳,岂止九千岁?’听得我们就像在东王府听证一样。”他也与一些以“睡眼惺忪或落魄文人面貌示人”的文科教授不同,对自身形象要求甚高,“每次来上课,必然是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煞清,中山装的风纪扣紧锁,皮鞋擦得裎亮”。
如今,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沈渭滨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了。但不管是回忆中,还是老街的粉墙黛瓦中,沈渭滨一直都在七宝,从未离开。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想与我们分享,欢迎联系我们。
联络邮箱:wx@mhbs.cn
(本期编辑 李成东 )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